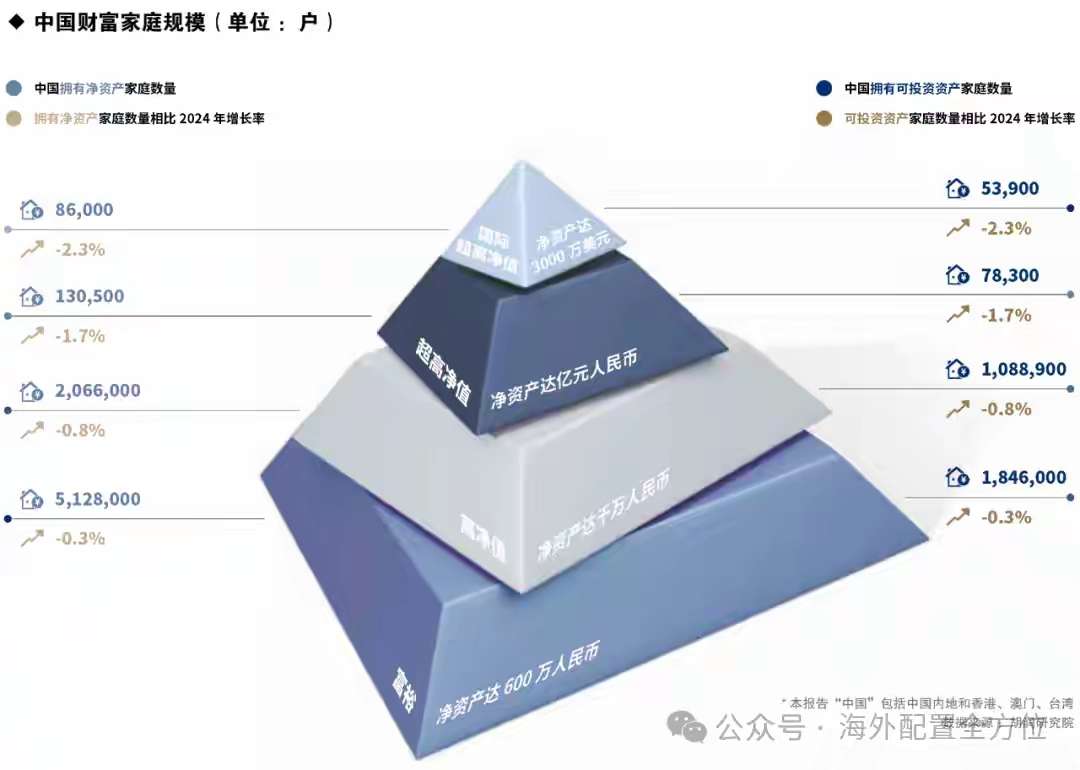以前的学生时代值得回忆的很多
现在的学生,机器人一样
十七岁的天空
九十年代初期,我们乡镇上有一所中学,里面有初中部和高中部,称为“竹中”。而到我们升入初中后,县教育局又在我们乡镇设立了第二所中学,只保有初中部,称为“港中”。这样,两所中学在一个乡镇上并列存在。但多多少少有一些区别。港中的学生接受乡下的孩子多,以及镇上部分学习不好的孩子,像施素琴,陆昆,在竹中留级下来的陆华,平常松等人。新港中设立在乡镇最东边,校区也是借用的校宿,教室都很老旧,校门锈迹斑斑。不过,晚上还是有专人锁起来。与其说不让学生出去,倒不如说不让外人进来。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经常有社会人员冲进学校捣乱。我记得当时最为出名的,有个绰号叫“大炮”的家伙。常常纠结了几个小地痞冲进学校,趴在教室窗户上叫某个女孩的名字。有时,也对男生下手。只要他看不顺眼,立马会冲进教室,扯着对方的衣领就往外拖。一边拖,一边打。班上个子最高的解春荣只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呛了一句,就在我眼皮底下被拖出去了。那架势,相信每一个从纯朴农村走出来的孩子都会心有余悸。我也曾被“大炮”扯过衣领。那天,在操场上,男同学聚在一起谈大炮的话题。因为当时大炮好像一直在骚扰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大家就在那八卦。我因为一眼憋见大炮从门外进来了,立马冲进正在津津乐道的同学群中,告诉他们大炮来了。可还没等我通报结束,大炮就到了我身后。一把扭住我的衣领,我想,这下完了,闭着眼等着拳头落下。好在当时上课铃声响了,老师们从办公室走出来准备上课,大炮也怕老师们,就放了我。大炮为什么怕老师?一来大炮当时的年龄也不是太大,对于年长的老师们,还是有所忌惮的。加上当时的校长曾经为这事报过警,大炮自然会知道分寸。 我们的班主任史庆森,先教的是数学,后来到初二时,教物理。史老师作为班主任,可以说威严有加。他的规矩是,无论是下课还是上课,教室内禁止大声说话。课堂上自然不敢多语,课间休息,如果被他看到或听到,必遭严厉的批评。他的粉笔头弹无虚发。这着实是让人惊叹的事。他只要听到有人在下面窃窃私语,无论他当时是背着黑板写字,还是在教室里来回游弋,他总会在第一时间弹出粉笔头。非常精准地落在目标的额头上。史老师上唇留一小胡,脸瘦长,有几分帅气,当时正与一体育教师谈恋爱。但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有点怕他。好在我物理成绩是所有课中最好的,老师自然是喜欢成绩好的学生。我记得史老师曾单独带我拜访冯荣展。荣展是不是当时的校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荣展在创建港中的过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史老师说,如果没有荣展的努力,就没有港中的建立。史老师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偏科太严重会影响总分的。我在学习上,其实重文轻理,但谁知道,我对物理这东西也痴迷的不行。导致我到现在家里的任何复杂的电路都能摸的一清二楚。像新房涉及到电工的,我统统自己搞定,喜欢弄各种灯的设置,让家里的灯光打出自己想要的效果。 还有一个老师在初中时也非常喜欢我。语文课老师何爱华。何老师喜欢我,自然是因为我的作文写的好。当时,进初中的第一个学生座谈会,大家围在操场上,何老师从小学毕业考试卷中得知我的作文得了高分,就在人群中叫我的名字。后来的初中三年,我的作文水平自然是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每每作文课,我的作文都会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被他拿出来进行讲解。就这样,在何老师三年的褒奖中,我的自信心也在一点点强大。不过,我最喜欢听何老师在课堂上的唠唠叨叨。这种唠唠叨叨和班主任史老师上思想课一样,看似不着边际地讲故事,实则在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做人的道理。走上社会,也和何老师有许多交集,那是后话。我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无论他是你的小学老师还是中学老师。 我的英语算不上太好,但也不算下游,在中间徘徊。这让我们的英语老师冯庆媛对我又爱又恨。冯老师是我们课程中唯一的女老师,而且她当时还怀着宝宝,每天挺着个大肚子上课。但她的火气又十分的大,动不动就对那些英语成绩一踏糊涂的学生在言语上进行指责。我倒没记得她骂过我。但我记得有一次她竟然在英语课上让我当着五十多个同学的面唱歌。起因是她在教我们唱英语歌,我正好被点名,她要求我试唱。但我不会,真的不会。读那些单词我都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让我拖着尾声唱出来,更难了。冯老师也不为难我,也没骂我,但要求我唱一首中文流行歌。当时有什么流行歌呢?像冬天里的一把火,黄土高坡,美酒加咖啡等等。我虽然内向,但老师的话一向是不敢不听的。选来想去,那就黄土高坡吧。然而,黄土高坡高音非常多,我唱了一半就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坐下来了。我满面通红,冯老师满面堆笑。 最不待见我的是数学老师沈正忠。天生对数字不敏感,尤其学到几何,那些证明题会让我证的非常崩溃。还有许多公式,我不是记不得,就是不会灵活运用。最后沈老师给我的评价是“满瓶不通半瓶摇”。也不知道他是夸我半瓶摇还是批我满瓶不通。反正那个时候没少挨他的骂。 同样的化学课也是,当时的化学课是一校长任教的。不知道是其教课水平有限还是我们学的不认真,全班的化学没有几个及格的。及格的就是那些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像昌栋,朱世杰等人。然而,昌栋在我们村考初中时,四个男生中,他是第四名。最顽皮的建中考了第一。后来,初中的语文老师何爱华对建中的评价是,此生智商高,悟性好,只需自己稍微努力,成绩自然会上升。说这话时,可见建中在初中的成绩不咋样,尤其是语文。 初中要到当时的镇上读,而且要住校。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出过村的孩子来说,有着太多的新鲜感。迫切希望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而做为大人们,却有更多的紧张,在那年的暑假期内,便商量着谁与谁家孩子睡一张床的问题。建中和长春是亲戚关系,不用说了,肯定是要睡一起的。六年级就四个男生,我和昌栋自然就被大人们安排在一起了。开学后,大人们组织几个家庭,一起包条挂浆船,装上竹床、被子,还有米,浩浩荡荡开往乡镇。米要缴到食堂,代伙。菜要用钱买。因为是新建校区,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都要在吃饭时浩浩荡荡块跑到乡镇南边的小学食堂去吃。谁曾想到,一个小小乡镇,在中午时间竟然会发生交通堵塞的情况,恐怕历史上也不曾有过。当时我父母亲一周六天给我的生活费是三块。早餐食堂有稀饭,是自己的米代加工的。自己从家里带瓶咸菜。午饭和晚饭的菜,对于我来说,青菜汤是吃的最多的,一毛钱一份。有时一毛钱也舍不得花,泡点开水,就着带来的咸菜下饭。食堂里有肉圆,五毛一个,吃不起,只有建中经常吃。周六回家时,我还省一点钱,买两个五毛钱一个的烧饼带给爷爷奶奶吃。从小就想着,等大了,对爷爷好一点。因为,从小就在爷爷的臂弯中长大,很喜欢他身上的味道,自己苦一点无所谓。可惜,等我有能力想孝敬他时,他已经在天堂静静地看着我了。也就是说,我一周六天只有两元的生活费。好在食堂打饭的阿姨,她儿子李迈也在我们班。而李迈又是我们几个玩的最好一伙中的一员,平时,阿姨没少往我饭盒里加菜。 学校大铁门边上,有个卖书的老头,没少挣我省吃俭用从二元里又省下来的一点钱。那老头当时好像就有七八十岁了,瘦削的脸,白胡须,有点像过去的私塾先生。不过,从老人的言谈举止中,可见其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课间我就喜欢蹲在他书摊前听他东侃西侃。从三国说到红楼,从李世民谈到李鸿章,绘声绘色。在这位老人家中的口中,才让我第一次体会到红楼梦的情感之美。不过,老人也卖一些杂志,当时流行《知音》。《知音》杂志大多谈及情感方面的故事。可能我是受老人讲解红楼梦中感情线的影响,对《知音》杂志中那些爱恨情仇总是欲罢不能。为了那点情素,我用省下来的钱买单。一边饿着肚子,一边喂饱自己的感性思想。其实,过早地接触那些与自己年龄不相符的情感,如果没有人正确地引导,不见得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好事。还是说说我与那些同学的事。每每想起现在处在天涯海角的他们,都会油然有一种亲切感。仿佛是,再远的距离,只要遇见,都会不加设防地亲近。 初进中学时,我和昌栋的床紧挨着建中和长春的床。他俩的争斗,我们自然是清清楚楚的。长春的个子高,在与建中时不时的吵架或动手过程中,建中明显处于下风。加上建中偶有尿床的习惯,就被长春拿捏的死死的。宿舍内有一盏瓦数很小的灯泡,昏黄昏黄的,从晚上到天亮也不熄。紧靠宿舍的门内放一粪桶,夜里谁要尿尿什么的,可以方便一下。导致一进宿舍,首先迎接你的就是一股尿味。但这些,对于从农村来的孩子而言,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让我受不了的是,宿舍内一到下晚自习后的吵闹声。我们男生宿舍在校园的最西边,里面住着来自四村八舍的学生。估摸着有三十人之多,可见,这三十多个孩子,在晚上睡觉时有多么地吵。 北张的汪有杏与丁远发,他们睡在紧靠门口的一张床上。两人的声调,常常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奈何我身单体弱,敢怒不敢言。汪有杏喜欢跳舞,当时流行跳霹雳舞。里面有一舞步,叫太空步,人就像在无重力下漫游一样,给人的感觉非常丝滑与流畅。我曾让汪同学在下晚自习后教我学跳这种舞。奈何天份不够悟性差,掌握不到要领只能作罢。 同学中有特长的又何止于汪同学,就拿我同村的长春来说,那书法了得,关健是无师自通那种。和长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但我从来没看出。到中学后,这个优点着实是让我惊叹的。因为我的字迹相当潦草,不要说一般人认不出,连我自己过个几天都无法认得自己写过的字。也想在暑假中自己下定决心去攻克这个缺陷。老天爷的意思是,你越在乎的,它越不给你。导致我现在有时需要签名啥的,都害怕别人笑话。至于长春的书法究竟是受谁影响?我也说不清,他有二个姐姐,好像也没怎么上学,父母务农。 班上另一个大神级人物陈松恒,这家伙彻底征服了我,会唱京剧淮剧,会画人体素描,会作画。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即使放到现在,也算作神童了。他唱老戏,字正腔圆,有板有眼。每当音乐课上,冯庆媛老师都会要求他露一嗓子。当初冯老师点名让我唱时,似乎有种淘金的感觉,最后我在黄土高坡的高音上破音后,金子的亮光在陈松恒身上验证了。我母亲就喜欢这种老戏,尤以黄梅戏最爱。我从小受母亲影响,自然对这类腔调不会太反感,甚至会喜欢。所以,当陈松恒在现实生活中,在他的嗓子里流出这种音调时,我着实是不敢相信的。我以为,那些在电台中,在舞台上唱出的曲调,又岂是普通人能够掌握与演绎的。我私下问过陈松恒这个让我放不下的问题。陈同学告诉我说,小时他父母亲见他有唱戏的天赋,曾经送他到戏团里待过一段时间,后来跟着师傅唱过几段老戏。因其父亲怕耽误了他学习,又被送回了学校。那人体素描又是怎么回事?陈松恒画素描,可用绝妙二字形容。他只要用粉笔在黑板上轻轻涂上几笔,几个人物的形象就栩栩如生起来。让你不知不觉地惊叹,他在下第一笔的时,全局就已经在他心中定型了。我在陈松恒宿舍里的床下发现了他有许多人体素描。有男人女人,有花朵,有瓶瓶罐罐。我是第一次在陈同学的人体素描材料中看见男女裸体素描。陈松恒同学的出现,大大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我对身边人的认知。后来学到孔子的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才知道,每个人都有其优点,而在当时以学习成绩论英雄的风气里,这种个人特长并没有太多的优势。那些成绩好让老师特别欣赏的同学,其实只是善于总结,找到了学习的方法而已,与社会的需要达成了一致,才会走的那么一帆风顺。陈同学初中没毕业,便缀学回家了,据说跟着父母亲开船去了,不甚了知。 我们那个班,真的是“人才辈出”。这里我只能加上引号,毕竟大家最后的出路大多数是在为了谋生而委屈自己做不喜欢的工作。施素琴就是其中之一。我所知道的是,她肯定不是以唱歌来谋生的,要知道,我们的音乐课都是她上的。我们所有的歌曲都是被她带唱出来的。我那首唱破功的黄土高坡,当然也是跟她学的。施素琴嗓门好,唱起歌来不吃力,让人听了很是舒服。也不知道她怎么会那么多的歌曲。说来也怪,只要被她领唱两到三遍,全班的同学都会唱。有次冯庆媛老师在操场上老远就听到我们教室在唱歌,特意回来告诉我们说,你们班齐唱时,那歌声太美了。施素琴是乡镇上的,从竹中转过来。何爱华第一次领我们读论语时,施同学由于读不惯那种语调,一边读一边笑。仿佛那些“之乎者也”古诗词在咯痒她,让她不禁笑出声来。当时施素琴坐在我后面,而和我同桌的也是乡镇上的王震同学。王同学可能家境富裕,从他的穿着上可见不是一般家庭的孩子,更为要命的是,这家伙抽烟。偷偷摸摸地抽。特别是上课前,他在坐上位置后,就会含一颗糖嘴里。第一次我会好奇问,原来是怕老师闻到他的烟味。晚上回家吃晚饭后回教室上晚自习时,身上会喷香水。我没少吃他的糖,也没少呛香水味。事实证明,王震善于与人打交道,虽然若干年后在同学聚会上他见到我时,经过反复提醒才想起我。大家的境遇不同,偶然的忘记也是正常的。 要说我们班最有领导能力的,恐怕要数当时的老班长平常松了。平同学也是乡镇上的,也是从竹中转过来,年龄好像大我们一点,听说当过兵。平同学能够当上班长,有一点可以证明的是,绝不是因为其成绩好才当上的。因为要算成绩的话,语文没我好,数学没昌栋好,英语没刘爱玲好,物理化学他更没有大多数同学好。那为什么他能够当上班长呢?应该就是领导能力了。平同学的领导能力,那还真不是一般的厉害。只要他在班上,都会遵从史老师的规定,不许喧嚣,不许打闹,不许在课桌间穿梭。我记得有次平同学在教室后面站在桌椅上整理黑板报,教室里有人在窃窃私语,就是那种同桌间的交流。平同学只是一个转身,眼光在下面一扫,全教室立马鸦雀无声,那种气场,确实没有第二个人能比。是军人的气质吗?可能是。后来在同学第一次聚会中,我喝多了点酒,说的话有些不由自己。迷迷糊糊中我听他对我说,好了,好了,说话别瞎说,要有分寸。确实是老班长。但我跟他的交集不多,平同学和长春,解春荣他们处的好。 小学时,建中坐我前面,虽不经常一起玩,但是一个村一起长大的,对他平时的了解太多了。但自从进入中学后,这家伙一次又一次的行为,总是刷新我对他的认知。冯庆媛作为一名女教师,上课穿裙子很正常,俯下身来辅导学生作业也很正常。然而,这个行为与这个动作被建中碰到后,就会发生另外一件不正常的事。那天,就在穿着裙子的冯老师俯下身子辅导建中前面的一个同学英语作业时,建中在后面用铅笔悄悄掀起冯老师的后裙摆。让冯老师的内裤在后面的同学眼中一揽无遗。惹的看见的男同学不自觉地哄堂大笑,女同学掩面偷笑。冯老师转过身来,不明就理。她不知道大家的笑声里藏着什么,很肯定懂得不怀好意。于是怒目圆睁,全教室立刻安静下来。这种恶作剧,建中似乎尤为擅长。终于有一次被校长逮住,当作全校的面检讨。事件是建中在男厕所内往粪池中掷砖块,让溅起的粪水沾到对面上厕所的女同学屁股上。可能是有一次溅到一位女老师身上了,于是告到校长那里。这种事,稍微查一查就知道了。于是我们的建中同学,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朗读起了自己的小作文。 初中学习生活中,我有三个死党,扣锁,志旺,梁桂赋。这四个人在一起玩不是因为成绩好,论成绩,我们三个肯定不如扣锁。当然,志旺与李迈昌龙关系也不错。只因有李迈妈妈在食堂的关系,才让我不至于一周只有二块钱而没菜吃。我们四个一起玩,也没什么出格的事。我只记得有一次我和志旺在操场上闲逛,听到初一的学生在上音乐课。我怂恿志旺说,我们冲进去,上音乐课的一般都是学生领唱,没老师的,谁也不知道我们是谁。志旺脑子一热就答应了。他在前我在后,等到他撞开人家门之后才发现是一名音乐老师在上课。但志旺已无回头路。我是立马三百六十度调头,脚底抹油开溜。志旺停在原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回来后,志旺一个劲骂我,我一个劲笑。后来我想想,四个人的志同道合,恐怕是喜欢撩拔女学生,那种将女同学撩开心又心甘情愿的那种。这些故事,说来话长,有些事不说也罢。我认为,十七八岁的学生,对于情感只是处在好奇心态而已。就像你在准备渡河时,河边有条花做的船,船上有人说,我们一起过去。明明知道,那是不可能渡的过去的,却还是被鲜花吸引。终究是要找一条信的过,又适合的船去过完自己的那条生命之河。有一次学校组织去看电影,电影的名字是《豆蔻年华》。回来后,何老师让我查豆蔻是什么意思。其实豆蔻是一种草,虽然很弱小,很它依然会开出小小的花朵。就像十几岁的青春一样,在懵懂的年纪里,也会学着牡丹花开是很正常的。 初二的下半学期,我们又搬到了乡镇西边的新校区。这个校区是新建的,红砖青瓦,排排教室崭新明亮。我和志旺睡上下床,成了上下铺的好兄弟。志旺的数学几何能力超级强,我的作文创作能力相当了得。两个人的不同优点,注定我们后来会走不一样的路。不过,我经常请教他证明题,也跟他讲我写作的心得。学校后面是一片田地,长满芦苇,部分长水稻或麦子。放学后,许多学生会去后面背单词,温习课文。到初三将毕业时,可能有其他故事在里面发生,这个只是听说,不能实证。像丁小健,汪忙粉,丁仁芳这些从初一就在一起同班的女学生,三年初中加起来不超过三句话。一是个人内向性格所致,其次,当时基本没有课外活动,很少有机会去接触与交流倒时毕业时,大家互赠了照片,才说一句道别的话。到新校区时,我们班迎来了另一批学生,就是志方中学的学生全部转过来。我们班接纳了差不多有十几名同学,像阿喜,素方,素兰,赵正国,沈根华等。沈根华就成了我同桌,坐在教室的最后面。沈同学的学习能力太强大了。在初三考高中时,他晚自习后会去学校前面的公路上跑一段路,然后回教室继续学到深夜。作为同桌的我,自叹不如。他就像一匹奔跑的骏马,我则像一头笨驴。后来听说他高中后考上了军校,我一点也不觉的奇怪。在我们那届同学中,考上大学的昌栋同学,沈根华同学,一个与我曾睡过一张床,一个与我曾同过一张桌。可是我都没能好好吸取别人的优点,结果是自己沉沦于社会涡流中,拼命为生计奔波。毕业晚宴上,老师们允许大家可喝点啤酒,丁远发好像醉了,我没喝,一个人独自回到农村。那段时光,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只是短短的瞬间,却总是会让人记得清晰。虽然路途各走各路,但终究是在自己的轨道前行。有时很想回到当年的十七岁,奈何,命运齿轮一圈一圈地咬合着,每一步都被安排的紧紧有条。当回忆成了消遣自身娱乐的时间,头发白了。那天阿喜从苏北来昆山,和淑方,淑兰,王长凤一起在昆山陆扬吃饭时,王长凤说今年马上就要领退休金了。众人打趣,第一笔的老人钱一定要拿出来请客。舍得舍得嘛,晚年生活才幸福。想起我的十七岁时,怎么可能会想到退休二字。那年十七岁的我一个人冒着鹅毛大雪,起早从家徒步三十公里去县城新华书店,就为了买一本散文诗集。是因为爷爷突然奖励了我十元钱,我舍不得花,想想县城的新华书店会有好看的书。等我抱着那本《十七岁的天空》散文集回到家时,已是夜里九点多了。父母亲着急,但他们视我为掌上宝。虽然是穷人家,他们从不过问我的个性发展。每个人的青春都是独一无二的,充满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瞬间和故事。当然,每个人的青春都充满了不同的色彩和经历。无论是挫折还是顺境,那只是生命的一部分。李白说:生者为过客,天地一逆旅。还有一段路,同学们,慢慢走,不着急,看看当下的好风景,因为,我们真的不会再重新来过。就当一回过客,作一段旅行罢了,生命还能怎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这世间告别时,不还是“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文中名字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