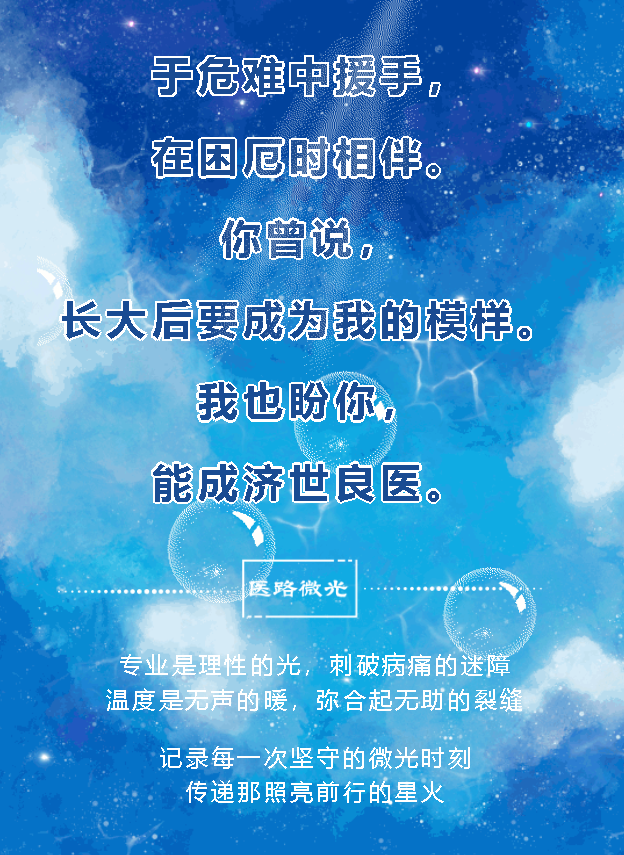
小阿卜杜萨拉木蜷缩在病床上的模样,我至今一想起来心就揪紧。十二岁的维吾尔族男孩,额头的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淌,把枕头洇出一小片湿痕,每一次呼吸都伴着压抑的闷哼——那是腹膜深处近3厘米的针状木屑在作祟。谁能想到,这枚尖锐的异物像颗藏在身体里的“定时炸弹”,哪怕轻轻翻身,都可能戳破内脏,抢走这鲜活的生命。
专家团队围着病历反复推演,每一个讨论的字都砸在我心上。我站在办公室窗边,目光总忍不住飘向手术室的方向,心里悬着的石头重得喘不过气。四个小时,像四个世纪那么漫长。直到主刀医生推门出来,声音疲惫却掷地有声:“异物成功取出”,手术室外突然爆发出一阵压抑的抽泣——那孩子母亲多日恐惧的释放,我紧绷的眼眶也跟着有些发潮。
手术成功了,可新的愁绪又缠了上来。听说小阿家境不宽裕,术后康复还需蛮长的路,我反复查阅他的病历,核对信息,生怕错过任何一个能申请补助的细节。当我来到病床边,轻声对小阿说“通过申请,昆山援疆帮你治疗费全免”时,原本咬着牙强忍伤口疼的男孩,眼眶“唰”地就红了。他用不太流利的汉语一遍遍地说“谢谢”,声音很轻,却重重砸在我心上。
出院那天,我刚走到病房门口,就撞进了小阿的目光里——那双曾因疼痛黯淡的眼睛,瞬间亮得像被点亮的星星。他一只手紧紧攥着衣角,另一只手悄悄从枕头底下摸出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画纸,双手捧着递到我面前。这是幅用蜡笔涂得五颜六色的画,线条歪歪扭扭,用铅笔写着歪扭的“感谢江苏昆山,援疆惠民好政策”。
“我……我以后也要当医生,像您一样帮别人。”小阿的声音小小的,却比任何誓言都坚定。我轻轻摸了摸他的头,接过画,指尖触到纸张残留的体温,“好,叔叔等着你,等你成为一名好医生。”
这张不算完美的画里,藏着最纯粹的感谢,更装着沉甸甸的生命之爱。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我们跨越山海而来的意义——就在天山脚下,种下这颗爱与责任的种子,等它生根、发芽,长成庇佑一方的参天大树。